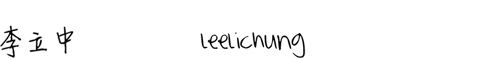如果有一種飛行
——李立中「夜間飛行」的歷史擬造
撰文/許楚君
李立中對台灣賽鴿史的研究,源自於他對鴿子歸巢本能的迷戀。從〈望你早歸〉、〈天使望鄉〉對鴿子歸巢的自我投射,到〈竹蒿山戰役與紅腳笭〉與「台灣空戰記事」系列,他則長期以馴鴿深入賽鴿文化,不只以攝影記錄鴿子返巢的飛行軌跡,在近期的作品裡更進一步將台灣賽鴿放置在歷史脈絡之中。
在「台灣空戰記事」系列,李立中重溯也重塑一段罕為人知的台灣軍鴿史。他收集史料,以此追溯1944年台灣空戰中參與期間的台灣軍鴿,以及隨政權轉移與開發衝擊而逐漸凋零的飛雁新村(即位於台南市永康區六甲頂的空軍眷村);與此同時,更讓他長期馴養的賽鴿循著歷史紀錄中的路徑,走過1944年空戰發生的上空,透過鴿背上的攝影機賦予空戰一種新的敘事。
虛構賽鴿史:一份喑啞文件的回聲
高俊宏在〈動物並不假清高:關於李立中與他的鴿子計畫〉一文論及李立中,認為他的作品深具回望歷史的潛質,不僅在於對歷史空缺的補白,更在於不困居「展演」殖民悲情的異質生產。考掘歷史顯然不應是藝術家的任務,而在於作品究竟是以何種姿態「回到」歷史,又如何在作品之中呈現出自身與歷史之間的距離。
這樣的異質生產,體現在李立中近期的作品「夜間飛行」。這系列作品以種種繁複的再現手法,乃至大膽的歷史虛構,重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日本引進軍鴿、美軍引進「空軍系」鴿種,繼而發展出賽鴿運動的歷史。
在這件「台灣空戰記事」最終章,更可看見所謂「異質」當然不僅在於李立中對冷僻歷史的深堀,也並非動物的敘事觀點如何擺脫了人類中心。關鍵或許更在,藝術家如何運用剪報、再製照片與文件,擬造出各種歷史偽證,由此反詰歷史敘事的真實。
延續「竹蒿山戰役與紅腳笭」等前階段創作,李立中此次更加清晰地把目光放在1944年10月12日上午發生在台灣的一場空戰。這是太平洋戰爭中日軍與美軍之間最後一場大型空戰,日本投入大量戰機與轟炸機而損失慘重,但在官方公報裡卻宣告為「勝利就在眼前」的捷報。在種種軍事誤判之中,有目擊者看見日本飛行員為防止飛機墜毀村落,將機身拉高而被美軍擊落。終戰之後供奉日本飛行員與台灣少年工成為禁忌,曾經的日軍「傳原通訊所」則成了「飛雁新村」,在土地開發的炒作之中面臨著拆遷的命運。
前述的歷史因由,透過散落在作品之間的剪報,隱伏在「夜間飛行」的敘事裡,藝術家則藉著更不為人所知的賽鴿史作為引線,以之為喻,回頭迂曲述及太平洋戰爭中殞落的飛行員、被犧牲與忽視的台灣少年工。
二戰中使用軍鴿的史料闕如,藝術家便順理成章「製造」歷史,將真實的剪報與刻意做舊的再製文件彼此混置,而由此形成了經過編造與杜撰的敘述。
再製的歷史剪報、文件陳列在入口不遠處的展牆,展場中心的座椅上則放著被重新改造、加上新封面的小說《夜間飛行》。這本法國作家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半自傳之作,寫及三架空航郵機飛行員在戰死之前的掙扎,並且藉由人物的陳述反思戰爭當下盛行的英雄主義。藝術家混雜真實與偽造的軍鴿歷史照片、文件,拼貼在小說的空白頁,由此截斷、再造小說所承載的意涵,以台灣的殖民史與之共振回聲,鋪墊出整件作品質疑戰爭敘事的基調。
歷史的漏洞:模擬飛行與身體勞動
以《夜間飛行》的敘事架構作為依託,李立中由此搭建起足以承載軍鴿及日軍歷史的敘事載體,透過模擬軍鴿的視角,來陳述在戰爭中人與鴿受到操控、不能自主的命運。
這段由賽鴿在執行模擬飛行任務時拍攝下的錄像,僅能透過鴿子所背負的錄影機,僅看得見不斷晃動、模糊不清的俯瞰影像、聽見周邊的風聲。李立中借取《夜間飛行》的飛行員視角,擬仿軍鴿的口吻重述了前文提及的台灣空戰,經由軍鴿之口讓歷史陳述中不可能呈現的主觀視角重現。
錄像裡的這段模擬飛行彷彿填補了一段空缺的見證,為被歷史遺忘的軍鴿發聲,在其間又投映著台灣少年工製造軍機的歷史殘影。然而,從作品裡的重重線索都可以看見這面由藝術家重重搭建起的敘事媒介,呈現的即是錄像敘事對於空白歷史的揣想。
藝術家不僅充分認知到這點,更藉著作品裡處處可見的毛邊突顯此一虛構性質。他在這段敘事之中刻意留下敘事的縫隙,讓放飛鴿子的片段、後設的歷史觀點出現在錄像裡。他將將飛行過程中的截圖,以凡戴克顯影製作成充滿懷舊氣息的作品,卻又藉著這種刻意的懷舊讓觀者知道,這不過是對歷史的想像。同時,觀者亦可在與虛構剪報相對的展牆,看見藝術家逐一為賽鴿畫下的素描、馴養的過程,由此知道整段錄像「產製」的始末。
李立中早從數年前即藉著親身飼鴿深入賽鴿文化。實際飼養鴿子、與鴿友交流的經驗,讓所謂「田調」不只是循線考察與側寫描摹,更成為一種身體力行的勞動。藝術家與錄像裡執行「任務」的鴿子所建立的馴養關係,則使得作品的歷史陳述變得更為意味複雜。
錄像藉著鴿子之口提到:「人類馴養了我們成就彼此的需要,建立彼此的關係,或許這是人類的渴望才轉嫁到我們身上。我們莫名肩負著成為一羽傑出優秀的軍鴿,為滿足人類的想像,甩不掉的宿命甚至無法決定自己的未來。」藝術家馴養賽鴿的紀錄於此成了自我揭露,坦誠地告知觀者,他如何從飼養、訓練,到派遣鴿子執行任務,完整模擬了歷史敘事路徑。
這無疑是對現實最深刻的介入與擾動。所謂擾動並非在於藉由挖掘無人知曉的角落來改變人們對既存歷史敘事的認知,更在於藝術家如何透過自己的身體、鴿子的身體,重新演示所有訓練與飛行的徒勞,並且經由與投身戰爭同等無謂的勞動,喚起觀者對這段敘事的共感。
「我愛的是吞噬人者」:史觀的迂迴險路
在觀看這些對二戰歷史的回視、被作品敘事策動情感之時,也切勿忽略紀德在為《夜間飛行》所寫的前言裡提及的「晦暗感」——亦即所有英雄主義的來源:「我愛的不是人,我愛的是吞噬人者。」
紀德說到小說裡「自相矛盾」的表述,是獨屬於戰爭中飛行員的矛盾:彷彿還有一種「有待挽救、更為永續的東西」存在於個體生命之上,等待著英雄去實現。即便一部分的他們也清醒意識到戰爭的徒勞與耗費,也不得不投身在宏大的歷史之流。小說中的主角李維耶將這樣的使命肩負於身,與此同時,當我們再看到聖修伯里在另一本以飛行員為主角的半自傳小說《航向阿拉斯》更清晰的反思,或許更可以明白敘事者如何強烈意識到戰爭中「勇敢」恐怕不是什麼太值得稱頌的美德。這種矛盾的意識顯露在小說裡,形成迂迴幽深的摺曲,因而產生了紀德所說的「晦暗」。
這種晦暗感原本就處處可見對台灣二戰史的種種陳述,在總力戰時期的台灣小說裡也不乏例證。李立中「台灣空戰記事」裡模擬飛行的視角,則更是明晰地呈現出這種迂曲的意識。
藝術家在創作自述中提及,他意欲重新梳理「被噤聲的歷史」,之所以可說這段歷史被「噤聲」,或許並不只在於當代人對歷史的認知空白,更在於接近這段歷史之路的迂迴與險阻:我們很難真的透過既存史料確切知道歷史事實,在戰爭罪疚與國族認同的裂隙之間,更難以查知所謂陳述甚至表態,究竟有多少真實的成分:見證者所說的有多少部分為真?在戰爭當下有多少來自於對動員的配合?
歷史的皺摺與陰翳,本就存在於整體歷史與個人歷史之間的衝突與掙扎。「夜間飛行」所觸及的更險之處更在於:陳述歷史之時,如何能免於受歷史戀物的心態所誘,又或者,被「人類命運」這道過於宏大的命題所吞噬?
循著這道思路再去檢視李立中對賽鴿史的追溯,以及對「環境與宿命」的醒覺,觀者彷彿也隨之在敘史的激昂情緒、虛構的清醒意識,這兩重的冷熱交替之間迷走一遭。我們於焉更加無法確知,「台灣空戰記事」這部微小的歷史,究竟在幽深拗折的歷史迷宮裡走了多遠。
|